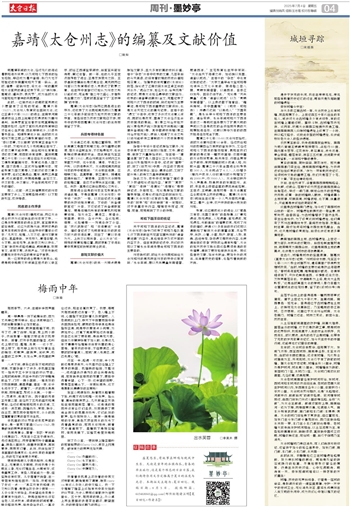□始知
明嘉靖年间的太仓,经过元代的海运漕粮和海外贸易,以及郑和七下西洋的始发归航,早已成为漕户番商、朱门大宅不可胜记的东南富域和天下第一码头。此时,编纂一部新州志,将太仓一域的富庶和太仓官民的德业记录下来,以“辨川原、厘赋役、谨兵防、表风节”,成为当时太仓州官和地方缙绅的共同愿望。
此时,一位悄然返乡的谢政官员使这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嘉靖六年(1527),太仓州人张寅致仕回到太仓,这位正德十六年(1521)的进士,在南京河南道御史任上因上疏触怒权贵被贬为唐州通判。后虽累官至右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国史检讨,经历了官场风波的张寅早已对仕途心生厌倦,因此早早返乡,以读书著书自洽。知道张寅返乡后,当时的太仓知州万敏立即上门请张寅编修州志。被“委以志事,交仪辟局”的张寅正准备大干一场时,万知州没几个月就调任吉州了,修志之事只能作罢。后任知州也有意继续修志之事,却因故未有结果。直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周士佐任太仓知州后,又请张寅重辑州志。张寅遂与邑人陆之箕、陆之裘等人,正式开始编纂州志。可能张寅及陆之箕等人之前对修志之事多有积累,他们汇集昆山、嘉定、常熟三县宣德、成化间诸志,并搜阅典籍、金石之文,访之故老,参之群议,于当年就完成了志书的编修。
那么,这部一波三折编纂而成的州志主要写了什么,又有哪些特点呢?以下抛砖引玉,权作导读。
同邑进士作序多
嘉靖《太仓州志》稿完成后,两位太仓进士欣然为这部新生的州志写了序。一位是与张寅同年的进士王积,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这位为政持大体、吏民怀畏的官员本来就好读书,他在序中欣喜评价该志:“凡天文、地理、人文之纪,吾州文献有征也,甚盛幸哉。岁月弥久,事绪日增,失今不载,后将无考,此新志之所以作也。”又言“新志所述昭远阐幽,阙疑儒信,核而有文,详而不赘,法则严矣。”对志书新成的喜悦与志书内容的肯定溢于言表。
另一位写序的进士更是大有来头,他便是明中晚期文坛领袖王世贞的父亲王忬,时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后官至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前一年,他的儿子王世贞刚考取了进士,正是家族荣光之际。王忬拿到志稿后也是对周士佐、周凤歧两位州官以及张寅等修志人员表达了敬慕之意。他在序中言辞切切地认为州志之所以能修成,完全是“惟二守之盛心,亦惟张先生辈之功”,落款时甚至留下了“王忬拜撰”的字样。
嘉靖《太仓州志》除两位同邑进士的序外,还收录了太仓同知周凤歧以及嘉靖二十七年前多部旧志及地方历史文献的序言。有些旧志及历史文献现已不存,而书中的序却因嘉靖《太仓州志》的流传而保留了下来。
兵防专卷特色明
太仓通江达海,地理位置特殊。而苏松常镇又是国家财赋之地,作为重要运粮港,若太仓盗贼生发,不仅贻患地方,也会影响运粮通道的安全。因此早在元至正十二年(1352),昆山州就在太仓城内立水军都万户府,统令定海、靖海、宁海三千户所,以防海患兵灾。太仓同知周凤歧在州志的序中感慨到:“太仓服在海隅,实咽喉之地,且属要害,联卫建州,特遣宪臣提兵临之。”意思是,正因为太仓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己才会带兵派至这里。可见,兵防一直是这位新任同知心之所系。
同样进士出身的州志主笔张寅当然深谙此理,于是在嘉靖《太仓州志》中专设“兵防”一卷,以突出记述太仓重要的兵防设施与事迹。下设的“兵备道职官纪”分目,不仅记述了兵备道职官情况,更是将境内所有的军事机构和军事设施,如太仓卫、镇海卫、军诸仓、军器局、教场、各千户所、各巡检司、烟墩、巡检铺等一一列词条作了介绍。在“历代武勋纪”和“平海事迹”分目中,编修者记述了元明季有战功的武将及较大的平海战事,突出了“事以平海为大,上兵之议用兵者,必从太仓”这一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同时表彰了平海战事中英勇驱敌斩贼的军士武将。
原始文献价值大
嘉靖《太仓州志》的另一大特点便是原始文献多,且大多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卷十“杂志”分目中收录的文章,几百年后的今天再读,依旧有着较强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摘录的宋郏亶的《水利论》段落,除论述了江南农田水利互倚互利的关系外,“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冈身”的记述,更是太仓地名最早的文献出处。收录的《通番事迹碑刻》全文,完整记录了郑和六次下西洋的时间、到达地域及主要事迹,是郑和下西洋重要的文献资料,也是太仓天妃文化的高光记录。在卷十的“遗文”分目中,收录了多份对太仓意义深远,同时也是改变、塑造了太仓经济社会历史面貌的奏疏。有《奏立州治安地方疏》《奏免贡产疏》《陈言地方利弊疏》《重建兵备道疏》等。其中都御史朱瑄《奏立州治安地方疏》,使后人知道了太仓之所以设州能够独立建制的六个历史背景和直接原因。
除卷十专设分目记述原始文献外,州志中常于正文之后附以档案、文书、碑记等,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如在卷一“建置沿革”附了邑人陆容议立太仓州内容。在山川形胜相关分目中,记述到“星野”时,附了《旧苏州》中同一内容的不同说法。记述到穿山、宝山、镇洋山时,又附了部分诗人的诗文及皇帝御制碑文。
除此之处,志书中还穿插了编修者不少按语和论述性内容,“寅按”“箕按”“寅曰”“海辨”“海潮论”“海塘论”等思辨记述,多卷可见。无论是原始文献的摘录穿插,还是论述性内容的附后补充,嘉靖《太仓州志》这样的处理,同现代志书的“附录”和“资料链接”有一定相似,对于丰富志书内容,增强志书可征、可稽、可信、可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目的佐证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内容记述,嘉靖《太仓州志》除专门收录了郑和及船队第七次下西洋前在天妃宫石壁所刻的“通番事迹碑”内容外,其他卷目涉及该方面的内容不多。但在有限的记述中,我们依然可以了解永乐年间朱棣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州志新成时,时任太仓州同知后任太仓州知州的周凤歧在州志的序中这样写到:“永乐年间,屡以天兵震叠东南诸蕃,更通西洋。”主笔张寅也在序中写到:“太仓当天下海道之冲,如运饷以足国,通番以威远。”在卷十的“杂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太宗文皇帝命太监郑和等统领兵二万七千有奇,驾海船二百八艘,赏赐东南诸蕃,以通西洋。自娄江口发舟,回日仍泊于此。”无论是“天兵震叠”还是“通番以威远”以及“赏赐东南诸蕃”,以上表述都不难看出,“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并最终达到“以柔远人”“万国来朝”,是永乐帝令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通俗来讲,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目的之一是明成祖朱棣为了扩展大明的声威以及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而开展的大规模航海活动。这跟以掠夺为目的的西方航海活动完全不同。
嘉靖二十七年(1548)太仓州志始成,彼时太仓建州已有50余年。经过历任知州的励精图治及军民的奋发作为,又经过郑和七下西洋的推动培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卷:农商并重的太仓物贸繁阜,贩夫走卒、行商坐贾穿流于街市;军民相融的城乡政通人和,科教兴盛(嘉靖二十六年全国进士科考录取300人,太仓就占了4人)、人口增多(境内户数与人口较建州时分别增加了近2000户,约7000人)。太仓早已跃升为人声鼎沸、物阜民丰的东南巨州。此时,来自海上倭寇盗匪的侵扰尚能控制,王世贞、王锡爵、吴梅村等一批太仓高官名士即将走上历史的舞台。嘉靖《太仓州志》就诞生在这样一个人气与商机并重,军卫、漕户、士绅、农户并存的新兴勃发的州地。
张寅,这位谢政返乡的进士,以“郡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的桑梓情,以“事无遗迹,物无遗轨,人无遗善,官无遗政,耳无遗见,光前信后”的编纂初衷,完成了州志的编修,使得470多年后的我们还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太仓的建置沿革、风俗节序、兵防、公署、乡都、物产、职官、人物、恩典、古迹寺观、杂志遗文等历史内容,也使得后世修志者“民物政治得有所稽”,太仓的地方历史文脉也因这些赓续连绵的志书编纂,得到了更好地保存与流传。而这些信史文献,如浮光跃金,更如长长的河流,流淌着历史的缩影,也指引着向前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