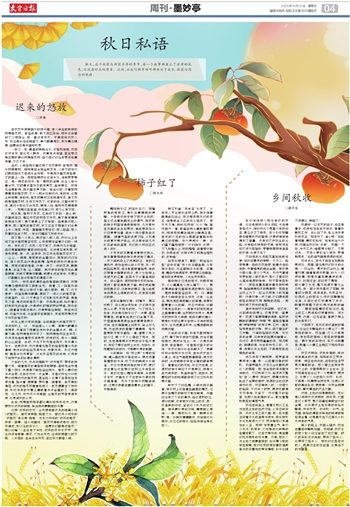□唐开生
车子缓缓驶入那条新修的村道。这条连接城乡的水泥路,光洁得有些过分,倒叫我这个耄耋之年的归客,莫名忐忑了起来。故乡秋收那幅原本喧腾热烈的画卷,仿佛被谁悄悄调低了音量。没有记忆中扬尘的土路,没有路边惊起的家禽,连那缕在记忆深处招摇的、带着柴草特有温香的炊烟,也寻不见了。
灰白色的水泥路笔直地向前延伸,将依旧青绿的原野一分为二。路旁是清一色的农家新楼,贴着光洁的瓷砖,安着锃亮的铝合金窗。样式虽大同小异,却个个气派。天然气管道无声地接入每家每户,取代了昔日场头屋后堆满的柴垛。我不禁有些怅然——那些在暮色里伴着母亲呼唤声、摇摇摆摆归家的鸭群呢?那些在谷场上为了一粒谷子而争斗的鸡雏呢?仿佛只是一夜之间,它们便连同那些低矮的瓦房、蜿蜒的泥路,一起被收进了历史的角落。
信步走向村外的田野。记忆中,这时候的田埂上,该是怎样一番景象?挤满了弯腰挥镰的身影,稻秆被割断时清脆的“咔嚓”声,扁担压着肩膀“哼唷哼唷”的号子声,汇成一曲丰饶而疲惫的交响。而今,四下里空旷又安静。广阔的稻田依然是一片炫目的金黄,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风过处,漾开层层叠叠的浪。那沉默的、磅礴的美,与往年并无二致。只是,侍奉这片土地的,不再是那些古铜色的脊背。
远处传来了轰鸣声。那声音浑厚而有力量,像一头巨兽沉稳的呼吸。我循声望去,只见几台收割机像巡弋的舰船一般,在金色的海洋里缓缓前行。它们所到之处,稻浪被齐整地“吞”入腹中,而后方,便魔术般地吐出了金黄的秸秆,饱满的谷粒已被悄然收纳。效率是惊人的,一片偌大的稻田,不过半个时辰,便被收割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行行整齐的稻茬,如同大地新理的平头,散发着植物根茎的清苦气息。
我站在田垄上,看着这现代工业与古老土地的庄严对话,心中五味杂陈。我怀念手工年代里,每一粒米都沾染着汗水的温度与艰辛;却也惊叹于这机械伟力之下,劳作竟可以变得如此从容。那种“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终究是被这铁铸的怪兽驱散了。这自然是好的,是祖辈们无法想象的好光景。只是,那份人与土地之间最直接的、近乎搏斗般的亲密接触,那份收获时混杂着极端疲惫与极致喜悦的复杂情感,似乎也随之被简化、稀释了。
我遇到一位本家的侄子,他正背着手,悠闲地站在自家田边,看着收割机工作。他认出了我,脸上绽开淳朴的笑容。“现在好了,省心喽!”他吐着烟圈,慢悠悠地说,“地承包给大户种,村里给我们发‘农保’。机器一下地,半天工夫,啥都弄妥帖了。不像过去,一家老小要忙活个把月,累得脱层皮。”他的语气里是满满的知足。
我点点头,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更远处。那里,曾经是我们孩子的乐园——打谷场。夏夜的打谷场上,铺着竹席,躺着看满天繁星,听大人们讲故事,那是我童年最清凉的梦。而今,场院还在,却已变了模样。一部分铺了水泥,整齐地停放着几台农机;另一部分被开垦成了菜畦,种着时令蔬菜,绿油油的,长势正好。场院边上的那条小河依旧静静地流淌,水色比记忆中清亮了许多,映着两岸整齐的驳岸与新栽的垂柳。一艘保洁船慢悠悠地划过,船上的工人熟练地打捞着枝叶。河水无声,仿佛一位见证者,看惯了岸上的沧桑变幻。
夕阳西下,将天边染成温暖的橘色,也给这片静谧的水乡镀上了一层柔和的暖光。村庄里,灯火次第亮起,有饭菜的香味从那些新楼里飘出。偶尔有轿车驶过,车灯划破暮色,载着从乡镇工业园区下班归来的人们。
我忽然明白,我所怅惘的,或许并非具体的炊烟、鸡鸣或手工劳作,而是一种正在远去的、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感联结。那个建立在艰辛劳作之上的、邻里相帮的乡土社会,正不可避免地让位于一个更高效、更独立、也更个人化的现代农村。秋收,不再是一场需要全民动员、充满仪式感的集体战役,更像是一份按合同履行的、高效精准的产业交割。
然而,土地依旧是慷慨的。无论是以何种方式被耕耘、被收获,它都在这个季节,毫不吝啬地奉献出它的金黄。这份源于土地本身的丰饶与静美,并未改变。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新稻的清香与柴油的味道奇异地混合着,这是属于当下江南水乡秋天独有的气息。
离乡的路上,我回头望去,村庄在暮色中静默如画。我知道,我怀念的那个故乡已经留在了记忆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带走了些什么,也带来了些什么。而我们这些老去的人,既是过往的见证者,也是当下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