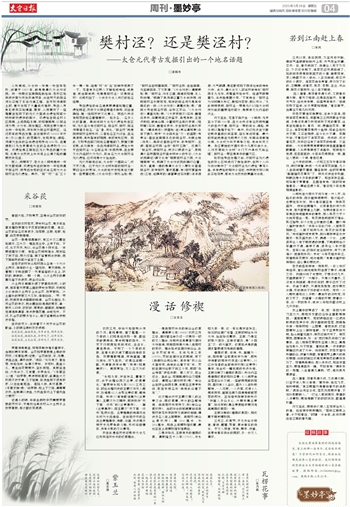□凌微年
众所周知,太仓市一中是一所百年老校,创建于1907年,前身是清代太仓州试院。市一中搬迁至南园路新址后,老校区地块被安排为开发改造项目,近在咫尺的樊泾河也实施了北延沟通工程。在开挖河道取土时,意外发现了大量瓷片堆积,考古人员急忙赶来实地调查、勘探,从而揭开了一座掩藏在地底下的元代大型瓷仓遗址和部分城市街坊遗存的面纱。该遗址在樊泾村小区西侧、上海西路北侧、致和塘南岸,以樊泾河为界,分为东、西发掘区,河西主要为原太仓市一中地块,河东则为樊泾村居民区。经过数年的考古发掘,在总面积达15000平方米(约22亩多)的范围内,发现房址、道路、河道为主体的各类遗迹现象近480处,估算提取以元龙泉青瓷为主的各类遗物约150吨。该遗址是江南地区元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太仓历史上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
那么,问题来了,老太仓人特别是市一中校友都知道,该遗址所在的原市一中地块属于樊泾村,而考古发现的正式命名却为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虽然, “樊”“村”“泾”三个字一模一样,但是“村”与“泾”的顺序却换了一下。笔者有多位熟人不解地或电话、或微信、或当面询问:究竟是樊村泾?还是樊泾村?这就引出了一个许多太仓人关切的地名话题。
考古遗址的命名通常要遵循地理位置、遗址特征、历史文化特征等诸多原则,突出准确性、唯一性和历史文化意义。而古代并没有规范的地名管理意识,一地多名,一名多义比较普遍。具体说到太仓元代遗址所在区域,元代至今有过樊村泾、樊泾村、樊村、樊泾河等诸多地名。“泾”者,河也,“樊泾村”就是因傍樊村泾而形成,二者地名互为衍生,且经常混用,其所指有时相同,有时有所区别。因此,文物考古部门和地名管理部门,根据文献记载,此处原有一条古河道樊村泾,遗址分布于古樊村泾(今名樊泾河)东西两岸,且主要文化内涵时代为元代,故命名为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应该说是十分恰当的。
元代开辟海运后,太仓称“六国码头”,成万家之邑。位于元代太仓城东部的樊村泾一带已经比较繁华,太仓的地方志和其他文献有一些零星记载。《太仓州志》(明弘治版)载:“樊村泾在城隍庙西。”“樊村泾桥,在岳庙南,元至顺四年,丁文彬建。”《太仓州志》(清康熙版)载:“樊村泾,州北三里,南通致和塘,北入杨林塘。”明确了其河道位置及水利作用,说明樊村泾长度可观,现存的樊泾河只是其中南边的一段。《太仓州志》(清嘉庆版)载:“洞庭分秀在樊泾村西,俗称江家山。”《太仓州志》(清宣统版)载:“《太宗哀册文》石刻:唐褚遂良书,旧藏明吴江史鉴家,吴宽有跋,王世贞购归,嵌弇山园,今置樊村泾吴氏宗祠。《枯树赋》石刻,唐褚遂良书,亦在樊村泾吴氏宗祠。”《镇洋县志》(民国版)在《寒溪清耳亭》条目下提及:明末“太仓四先生”之一的盛敬(号寒溪)居住在南园北边的樊泾村,与顾士琏(浏河人,晚年迁居樊泾村东,故号樊村)、王御(居樊泾村西)合称“樊村三隐”。还提及“樊泾村,傍樊村泾,民多以耕读为业”,表明清代至民国樊泾村呈半城半乡的形态。《太仓试院碑记》碑文也有“相度樊村泾之西,太仓塘南岸”句,明确了太仓州试院的确切位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太仓文人萧抡也曾居樊泾村,故号樊村,著述甚富,有《樊村草堂诗选》三卷,他撰写的《通蕃事迹石刻歌》洋洋洒洒,大气磅礴,是讴歌郑和下西洋壮举的诗咏力作。此外,清太仓文人邵延烈有诗句“樊村西北九龙东,绣雪堂开地半弓。话语芳踪题壁处,流传胜是碧纱笼。”下有诗注:“樊村泾为州城巽水所汇,康知州莅娄,即议开浚。”凡此种种表明,樊村泾一带是元代以降太仓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文化内涵的沃土。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产生一个疑问:元末至今不到700年,且太仓并没有经历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樊村泾一带的瓷仓、道路、房子何以掩埋于地下?虽然,我们无法在文献记载中直接找到答案,但也有迹可循。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元明易代之际,东南沿海群雄纷起,太仓成为兵家常争之地,饱受兵燹之患。浙江黄岩的方国珍势力几度攻袭太仓,从刘家港到太仓城“千门万户俱成瓦砾丘墟”,樊村泾一带正是其中的重灾区。
抢救性考古发掘之后,对樊村泾元代遗址的核心区域进行了原址保护,在两个入口处设计制作了“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景观小品,另有遗址的相关介绍栏,市民朋友可以到此实地观赏,感受太仓历史的厚重与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