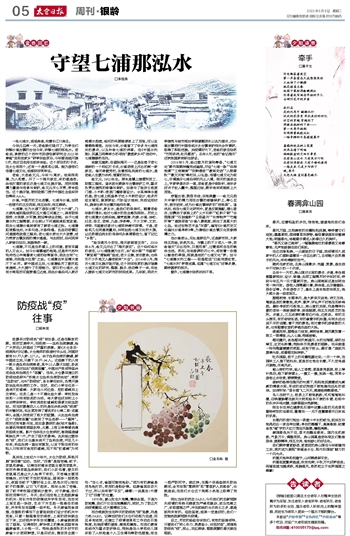□陆钟其
我最早对防疫战“疫”有印象,还是在解放初期。那时百废待兴,而疫病——血吸虫病肆虐,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据《太仓县志·疫病流行》记载,太仓南郊的独溇村牛头泾,民国时曾有60 户人家、227人。由于血吸虫病的肆虐,新中国成立后,只剩下38户、94人。这些剩下的人有一部分是血吸虫病患者,其中23人腹大如鼓,卧床不起。面对如此“疫病恶魔”,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决送走血吸虫病这个“恶魔”。当年,太仓最早建立的防疫站名称叫“苏南太仓血吸虫病防治站”,简称“血防站”,也叫“防疫站”,县长兼任站长,负责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当时,我们小学生任务一是消灭钉螺蛳:大家在小河边捡、挖钉螺蛳后上交学校;任务二是一个不漏化验大便:学校发油纸和一小张有姓名的白纸,将大便包好后附上小白纸带到学校,学校再把钉螺蛳和粪便交到血防站。而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则是在决战决胜“疫病”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全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此血吸虫病这个“疫病恶魔”也就有了专业名称——“瘟神”。那时还有电影问世,我印象最深的是《枯木逢春》,由著名导演郑君里执导,尤嘉、上官云珠等著名演员担纲主演。影片当年在太仓放映时,剧院里是嘘唏抽泣声一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经过数年战“疫”,我们太仓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并且几十年来,吸血虫病一直没有复发,以至于现在有的年轻人只知有可食用的螺蛳,而不知“钉螺蛳”为何物。
其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太仓为防疫,积极开展“除四害”运动。当时,“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记得当时捕杀老鼠主要用老鼠夹,有时夹得老鼠血淋淋的,我们小孩怕看,要交的老鼠尾巴是让大人给弄下来的。灭苍蝇主要用苍蝇拍,对付蚊子当时用面盆,里面涂一层肥皂水,夜里在蚊子飞舞时迎上去,肥皂水可以粘住蚊子的翅膀,让它飞不起来。那年头拍了苍蝇、捉了蚊子学校里还要统计数字。对于麻雀,我们那时用弹弓打。冬天,我们在空地上支起捉麻雀的机关:用长方形的砖围成井字形空间,在空间上面支起一块砖,支点下方支起一根悬空的细枝,井字形空间里撒一些米粒。冬天麻雀觅食困难,在饿极的情况下会冒险到我们设计的机关中觅食,只要一触碰悬空的细枝,上面的砖块就会压下来,正好把井字形空间覆盖,小麻雀就被困在了里面。记得那时,新华街上的熟食店里有油酱麻雀卖,5分钱一只。特别是深秋初冬时节的麻雀十分肥硕鲜美,只是买好后,售货员会提一句:“当心点,雀里可能有枪砂。”因为有的麻雀是用鸟枪打的,使用的是铅砂弹。但麻雀其实功大于过,所以后来被“平反”,蟑螂(一说臭虫)代替了它“四害”的位置。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震惊全国。于是为防地震,我们不仅住在地震棚内,同时,为了防止灾后疫情蔓延,还大搞清洁卫生。
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的防疫战“疫”场景,则是力战SARS。记得当时我们太仓行动极为迅速,而且卓有成效,还建立了疫情信息和工作动态日报制度,杜绝疫情的缓报、漏报和瞒报。而我们教育系统作为重点防护单位,特别是在小学和幼儿园采取了入校检查个人卫生情况等防范措施,师生一起严防死守。就这样,在整个非典型肺炎防治期间,全市实现“零病例”和“零医护人员感染”,也就是说,在我们太仓这个局部小战场上取得了完胜。
相比当年的抗击SARS,今天我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无疑更加严峻和复杂,波及范围之广,采取措施之严,冲在前线的白衣战士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我坚信,结果一定是好的,我们一定能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总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只要我们“同心协力、英勇奋斗、共克时艰”,顽强地防疫战“疫”,那么,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