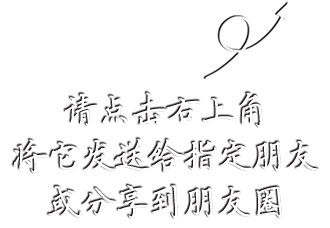□韩晓玲
从我买了一套理发工具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无师自通地成了家里人的专职理发师。家人们不必筛选理发店,也无需等待理发师,因为我随时随地可以出摊,成为他们的专属发型师“托尼”。
给家人理发,是一种别样的亲情交流。手里的活儿不停,嘴上的话儿不歇,谈谈工作,聊聊生活,包罗万象,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情感的方式。对方乖乖坐着,任由我“摆布”,而我的“技术”也要保证等会儿能让“客户”满意地站起来。记得第一次给儿子理发,我兴致勃勃地告诉好朋友我的“新手艺”时,她却调侃我说:“他今儿个出门了吗?”对我的理发手艺满是怀疑。理发需要耐心,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造就一片“地中海”。当然也少不了审美的参与,好在家人们对自己头发有固定的审美眼光。如果说刚开始的满意度其实多数是宽容度,那么随着练手次数的增多,后来真正的满意度也就大大提高了。
然而“托尼”也并非百无禁忌,正月里是不能开张的。我不知道外面理发店是不是也受此影响。祖母曾告诉我,正月里剃头,会剃出“蒸笼头”,导致这孩子今后脑门上一直汗涔涔的,活脱脱一个蒸笼,是调皮贪玩的表现。而老人们总是对下一代寄予厚望,这样调皮贪玩的主儿是要不得的。因此,头发再长也要憋着,憋到二月初二“龙抬头”这一天。这天理发,寓意鸿运当头,辞旧迎新,纳祥转运,出人头地。如此一来,这一天大家可能就会扎堆去理发,这可忙坏了正月里有点闲的理发师们。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的日子,在屋边找一块草坪,扎上帐篷,搬出桌椅,摆上茶具果品,边露营边出理发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光照充足,在习习微风抚摸下,头部平时被忽略的角角落落也一览无余,最后的成品自然更加有型。时间似乎花不完了,理得久一点、再久一点也不会觉得劳累厌倦,成了一种惬意的享受。理发结束后,喝喝茶,唠唠嗑,露营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了。
父亲住院的那段日子,他头发长得很快,包扎和涂抹药物变得麻烦起来,于是,我又出摊啦。直接全部剃光,简单快捷。旁边的病友经过门口时看到,以为是医院提供的上门理发服务,不禁啧啧称赞,就差进来排队了。
记得有一年冬天,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我在室外给祖母理发,邻居家的老太太刚好来串门,见此情形,露出羡慕的神情,说也想试试我的手艺。本来我的服务对象仅限家人,但祖母热情慷慨地夸奖并推荐我,我不忍拒绝,于是便得到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理的是满头白发。得到外人的赞赏,更是提振了我作为家人理发师的信心。后来,老太太过世了,但在冬日暖阳下理银丝的画面,依然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充满灿烂温情。
给家人理发,只是寻常岁月的素淡,不随世界变化而更改,不因岁月迁徙而转移,宛若一杯温水,总能带给人一抹世事相安的静谧。